晷时印迹——周吉荣艺术展研讨会
时 间:2024年4月18日下午
地 点:湖北美术馆四楼艺术交流中心
主持人:刘礼宾 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教授
发言嘉宾(以发言先后为序):
冀少峰 湖北美术馆馆长
殷双喜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鲁 虹 合美术馆执行馆长
杨小彦 中山大学教授
孔国桥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张广慧 湖北美术学院教授
祝延存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朱 橙 批评家、策展人
蔡 萌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策展人
周吉荣 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教授、本次展览的艺术家
刘礼宾:大家中午好!今天召开“晷时印迹—周吉荣艺术展”研讨会。首先介绍现场嘉宾,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殷双喜老师,湖北美术馆馆长冀少峰先生,合美术馆执行馆长鲁虹先生,中山大学教授杨小彦教授,湖北美术学院教授张广慧先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祝延存先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蔡萌先生,批评家、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朱橙先生,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孔国桥先生。我是本次会议主持人刘礼宾。
周吉荣老师是中央美术学院二级教授,是著名的中国当代艺术家,最早是以版画创作为主,后来转向架上绘画。十几年之前,他把纸浆等综合材料作为他创作的重要方向。研讨会的最后会播放一段视频,是周老师在西北的实践,用风等不带电的方式创作的一批环境版画,这次展览没有展出。
此次展览的主题是“晷时印迹”,表达了周吉荣老师在创作过程中对于时间、空间有着非常强烈的感受,将现实感的感受,通过他的描画转变成超现实的状态。尤其是80年代后期的作品,因为体悟对象的方式不同,以及对于文化、对于传统的判断,他的作品慢慢出现了一种超越性体悟。2019年我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策划了“历史的清唱 周吉荣个展”,展览主题是“天人之际”,从展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西北的荒漠、戈壁滩等都进入他的创作视野,不仅体现了他艺术创作语言的脉络,还表现了他对文化传统的追思、追忆,这是周吉荣老师非常重要的特色。
下面就有请各位嘉宾针对周吉荣老师的创作阐释或者提出自己的观点。首先有请冀少峰馆长。
冀少峰:谢谢主持人刘礼宾教授,感谢各位专家莅临研讨会。这个展览筹备了两年多,对艺术家来讲,如何在一个美术馆的空间把自己40年的探索表达出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周吉荣作为新生代代表艺术家,1987年大学毕业就确立了自己鲜明的艺术风格,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作为贵州人来到北京,看着胡同一个一个消失,对北京城急速的变化痛心疾首。他用图像把这个过程记录了下来,在图像的背后可以看到他隐隐的伤痛,这是成长之痛,社会发展太快了,传统文化的撕裂对他的影响很深,这是一以贯之地隐藏在他图像背后的精神。在确定了这种视觉符号的标识以后,他又转向了海市蜃楼系列,由实到虚,由具象到抽象,有回忆的伤痛,看似虚幻缥缈,但是又让人感觉到急速变化的社会发展现实所带来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变化。另一个印象深刻的系列就是他的“中轴线”系列。周老师居住在北京东帅府一带,他对北京的中轴线了解的比较清楚,他作品的中祈年殿、城楼、宫殿、角楼,都是他对城市变化的思考,用摄影的方式多角度的表现一种虚幻的变化,让人感知到一种触目惊心的变化。
把周吉荣归类为版画家不太准确,他已经超越了版画和复数的概念。他的作品不是复数,但有了强烈的时间印迹,它都是独一无二的。有对竹子、纸浆的探索,从《故城》系列可以看到综合材料发生了重要作用。周吉荣非常接地气,他把当地的土、石头直接搬到他的画布上,和当地的材料相结合。由此,从这40年可以看到周吉荣的视觉图像变化的过程,他由具象到抽象、由叙事到非叙事、由平面到立体不断进行视觉转换的变化,并一步步把版画解放出来。他给此次展览取了一个诡异的名字“晷时印迹”,这是时间的痕迹,在他的作品中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个主题体现了艺术家的传统文化修养,胡同、角楼、中轴线、西北故城的景观都是对传统文化在迈向当代社会过程中被撕裂的思考。比如作品中角楼被不断覆盖,就是传统文化一层一层被覆盖,最后都面目全非了。《画论》上讲画实易,画虚难,如何把思想用图像表达出去,其实是很难的。
纵观周吉荣40年的艺术探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断进行自我超越的艺术家,一个不断颠覆版画表现领域的艺术家,一个精于思考、勤于变化并不断在变化中向前发展的艺术家。此次展览是周吉荣的一个阶段性总结,虽然没有展出全部作品,只是一部分,但是基本上可以看到一个艺术家伴随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所取得的变化。
祝贺周吉荣,也感谢各位与会的专家,谢谢!
殷双喜:对周吉荣先生的作品,我其实一直在关注,但没有特别密切的关注。周吉荣待人做事很诚恳,他没有与当代艺术家们扎堆在一起,保持着一种距离感,这个距离感来自于廓清自我的认识,他始终把日常生活和历史的回应拉开距离。我最早看到他的作品是他的北京胡同,这种题材中央美术学院的很多人也画,包括王玉平画北京的写生、现场的写生。中央美术学院一出门就是老北京,老北京成为美院学生和教师的创作题材是非常自然的。在这个过程中,周吉荣的创作有一种距离感,这个距离不只是作品本身的题材,还有他自身的观察。当时他们那拨“新生代”,还有“近距离”,他笔下出来的作品,没有那种强烈的价值观、歌颂或批判,感觉他是很冷静客观的呈现。但有一种超现实的特征,和日常生活的具象再现拉开了距离,他是以一种图像符号,表达了对历史的回望和远距离的凝视,“凝视”这个词比较符合他的创作状态。所以他后来做的主题性创作,包括观景台、天眼都是观和看,都是凝视,凝视什么?凝视永恒的时空。或凝视或是仰望,仰望星空,凝视历史。他在热情中间保持冷静,中央美术学院有一个特点——有若干个贵州画家很有特色,田世信、曹力、王华祥、余陈等一批艺术家在央美都特别有个性,不随大流,都有强烈的个人特点。周吉荣在其中属于比较温和的,但是他原来的个性特别强,他表达的情感很平缓,随着历史时空的推演显得很平和,我们仰望星空,天上的星星似乎不在动,但我们不知道这些星星运动的速度有多快。他有一个系列作品叫《海市蜃楼》,他在思考存在和虚无,即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这是学院派的艺术家应有的艺术深度。他和我们理解的那种特别时尚的、很惊艳的当代艺术相比,显得比较温和,他带着历史文化背景的眼光去观看现实,他的作品平静且有一种穿越和穿透。“天眼”放在贵州是具有象征意义,因为现在贵州的山水地貌、经济发展是受限的,工业基础不强,但是东数西算,天眼放在贵州,也的确有很超前的方面。
周吉荣的创作思考穿越了当下,更重要的是回望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寻找历史的记忆,即确定我们的身份、确定我们的方位。“天眼”发现了很多恒星或者行星,这些星星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它是未来天文学的一个定位,就像现在的“北斗”系统,我们有几百颗卫星才有一个全球的定位。周吉荣的创作在这个意义上,着力于历史性的回望和思考。至于他在版画语言材料方面的探索和创新,是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的传统,特别开放,鼓励学生创新,没有太多限制。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展中,版画系学生的作品是很难分辨的,如果不是学校规定版画系毕业生的毕业展必须要有传统版画,观众进了展厅会弄不清楚是哪个系的。像材料、雕塑,版画系的学生都可以做出来,既聪明又重视能力,这是版画系很好的传统,非常的开放和创新。周吉荣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他打开了思路去做,没有必要再强调这是不是版画,只要是绘画就行。
如今版画不是特别热门的画种,虽然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艺术门类,过去它是革命的工具和武器,它的批判性是很强的。但是在和平时期,版画怎么样去传达建设性、建构性的特点,这对中国当代版画来说,走在前面很重要。尤其像周吉荣这一代60后艺术家,承前启后。因为老一辈艺术家都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新兴版画是革命的工具、斗争的武器。如今版画如何参与当代文化的建构,对于普通观众来说,版画的技术、材料如果没有工作室的实际体验,很多观众觉得看版画展还是看图像,还是画家呈现出来的图像。所以周吉荣的“海市蜃楼”中的都市大部分是暮色苍茫,他仰望历史的眼光穿透得很远,有一种悲怆的意味在里面。这个背后看到了历史,让观中重新去判断,我个人很难判断他的画是悲伤的还是批判的,对待历史文化的概括,他是一种呈现,每个人去读都有自己的感悟。
鲁虹:首先谢谢主持人,并祝贺周老师。因为很多年前在深圳美术馆做了过四方工作室的展览,所以当时对周老师的作品《胡同》系列有很深的印象。不过这么多年跟周老师没有联系,对他的创作也不了解,所以我一直对他的印象就是“胡同印象”。但我昨天一看展览,发现完全跟我以前理解的周老师创作不一样了,他的作品表明他一直在不断推进,而且都是从版画角度出发。我昨天还问他,早期做《胡同》是否受到日本版画家斋藤清的影响,他说没有。按我猜测,那个时候外来风格多多少少对他有是影响的。我还认为他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品应该是《景观》系列,这一系列的作品都是表现具有历史感的北京古建筑,制作方法首先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然后将多幅图像叠印在一起,相比早期的《胡同》不管是在题材上还是在风格上都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东西,非常好!我注意到,有好长时间,他一直在做版画,比如关于天文馆的版画,无疑还是在版画的概念上做文章。但我一看他的展览,我就在想这是版画吗?根本原因还是我一直带着对《胡同》的印象,但仔细一想我感到他其实还是从版画出发的,他早期在布上是尝试将印痕与绘画结合,并在开创新的表现风格。看的出来他对版画“复数”的概念不再执着了,原因是在早期工业印刷发达的情况下,比如在延安需要把一个作品印出来让很多人看到,故那个时候版画的“复数”概念很重要。但是在图像时代与印刷高度发展时期,周老师与一些版画家开始放弃“复数”的概念了,但印痕仍然还是很执着,无论是先把印痕和绘画结合,还是后来以画为主,他内在的版画家逻辑一直在里面。我昨天看展是倒着看的,因为1号展厅有些画还没挂完,相对而言我对2号厅印象更深,也觉得2号厅做的特别好。与其他人在纸上作画不同,他是把制作纸浆和创作过程融为了一体,由此也创造了属于他个人的独特画种,现在应该叫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新近的作品常常借助于自然力量,比如《竹》系列,就运用了自然的元素,更加上有传统“竹”的文化背景起作用,所以别有一番意味。除此之外,他还画了一批西北风景,既有历史感,也有时间的厚度。有一点很重要,即他画画用的并不是丙烯、水彩等,而是取自于当地不同颜色的土,再加胶分层涂抹后,就产生了一种力量感与冲击力。也有很多人做综合材料,但更多是学他的形式,更多是执着于材料本身。在这方面周老师很有启发性,而且他确实给绘画开拓了新的道路,可惜的是他有一些非常好的作品没能展出,据我所知在这些作品当中,他利用大自然中风的力量,达到了特殊的效果,真的非常好。尽管这样,我还是非常震撼,我对2号展厅的作品特别感兴趣,我希望以后周老师那一批创作能够跟观众见面,我想过几年有条件的话,我们会再请您来武汉展出。
杨小彦:我在中山大学教了20年的书,主业是传播学。版画是一种真正的媒介。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到了版画的危机。版画所面临的一个极大的危机是版画的主体性的消失。我们应该知道,版画的危机根本原因是它是一种地道的媒介。今天是一个泛媒介的时代,从中央美院到广州美院,有几个中年学者都在讲媒介,讲媒介竞争。版画不需要特别讲媒介,因为版画就是媒介,版画的问题就是媒介的问题。
谈到版画,就要先讨论一下摄影。摄影是版画的延续,摄影的发明者尼埃普斯最重要的成就是发明了日光蚀刻法。日光蚀刻法就是一种版画方法,后来发展到直接把光线的强弱变成一个版,就有了1827年第一张照片。如今是AI时代,蔡国强这几天正在温哥华做一个展览,就是利用AI来工作。不过我要说,周老师其实是AI的先行者。在美术界,有不少人尤其是老一辈艺术家认为画画是不能画照片的,画画一定要画模特。现在的年轻人只能画照片,连美院考试都是在画照片,美院评卷也是把考卷输入电脑再评。要知道电脑本身就是一种色彩处理,电脑处理过了,又如何能评?玩摄影的人都知道,摄影就是一个处理过程,色彩进入电脑,经过程序处理,不知道如何利用这样被处理过的电子文件来判断一个人的色彩?反过来说,在周老师的创作中有摄影的元素,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他关注的是媒介,他所从事的是一种媒介实践。今天一个艺术家不一定是画家,一个画家就是画家,不一定是艺术家。重要的是如何处理你的对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有什么样的媒介。所以我认为,版画家比其他画种要更加前卫、更加先锋,因为他们必须更加敏感地去面对媒介本身,去寻找和挖掘媒介的可能性。我在写周老师的文章中专门谈到“期待物质化”的议题。摄影就是时间的切片,而这也是一个版画的概念。所以一个版画家一定会对媒介本身有非常敏锐的感觉,一直在媒介的变化中寻找可能性,所以他绝对不会恐惧AI,不会过于考虑手上描绘功夫是否消失,不会去想,你是搞照片的,所以你不是艺术家。今天是一个泛媒介的时代,媒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媒介的角度看,对象要化身为载体才能成形。
现在看来,周老师一直都在寻找媒介的各种可能性。这样一来,他由媒介上升到造纸,对纸质可能性的追求,也就不足为奇了。我曾在周老师的工作室,听他讲造纸,不是简单的造纸,造纸本身就是作品成型的过程,而不是造纸张,是纸张这种材料如何与各种有机材料相结合。我看了非常感动。这不是简单的造纸,而是一种媒介的实践,目标是媒介,不是造一个载体,在上面画画。这就是版画超乎寻常的一个特质,在这方面周老师是大家。今天,是AI时代、大数据时代,恰恰是以媒介为重要工作方式的艺术家大展宏图的时代。摄影出现时,人们质疑摄影,它是艺术吗?其中最著名一句话就是摄影没有灵魂。我不知道什么叫灵魂,但我认为恰恰是媒介的发展在推动艺术的发展。最后,讲一个媒介学的基本概念:媒介技术决定知识形态,媒介的发展决定艺术的新语言。
孔国桥:谢谢主持人。上午去展厅,看了周吉荣老师近40年的创作成果,感觉很震撼。也许是因为和吉荣有着相同专业背景和相似专业经历的缘故,对于他的艺术探索,我有着一种天然的理解和认同。而吉荣长期的艺术探索历程,也在事实上体现了中国版画近五十年来所经历的种种问题和困扰。在其中,有起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对于版画“本体语言”的强调,也有随之而来的有关“版画困境”的持续讨论……而吉荣的艺术探索和实践,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显出一种特别的意义。
从吉荣的本科毕业创作《北京胡同》系列开始,以及之后的《飘逝的记忆》和《最后的纪念》系列,还有起始于2013年的《景观》系列等,吉荣大量使用摄影图片展开他的创作构思,并形成了独具其个人特色的作品风格。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丝网版画本体语言的深入研究和丝网专业技法的娴熟掌控。而从2002年开始的《海市蜃楼》系列,再到后来的纸浆综合材料作品,及至他目前正在进行的在麦积山、炳灵寺等现场而非艺术家工作室实施的《风 迹》系列,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一步一步地扬弃版画的“规范”。刚才殷双喜老师讲,版画曾经是新中国美术创作中特别重要的一个艺术门类,在中国艺术界也曾占据了重要的话语权力。我想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在1949年之后,受鲁迅精神感召的一代木刻青年,特别是从延安鲁艺走来的版画家以及有过版画创作经历的美术家们,已然成长为中国各级美术机构和各大美术学院的领导者。但是,随着他们这一代人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版画也随之失去了在中国美术界的主流话语权力。同时,上世纪90年代之后逐渐形成的中国艺术市场,版画的复数性——这个在革命和战争年代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版画特质,却成为了版画在艺术市场上缺失商业价值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版画界有关“版画困境”的持续讨论,至少体现了当时的版画家在面对这一境遇时所引起的一种心理失落与情绪焦虑。我不知道吉荣是否有过这样直接的失落与焦虑,但我相信,在吉荣从版画走向综合的过程中,必然有其个人在当时的语境下对于这一问题的严肃思考。因为真正有艺术追求的版画家,在他们的心底,是把版画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的手段而非样式。即如我们考察世界范围的版画作品,“版画家的版画”和“艺术家的版画”,其艺术追求和作品气质,也往往是两种层面的呈现。在这里,贯穿着吉荣艺术探索和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所谓的“版画思维”,这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个点,也是他在长年投入版画本体语言研究和围绕艺术创作思考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思维底色,是他从“版画创作”转向“艺术创作”过程中的思想痕迹。
另外,在周吉荣老师的作品中,我还读到了一种我所特别推崇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态度。需要强调的是:我在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并不是美术史上的某种风格或某个流派,而是一种对于艺术的现实主义态度。在上世纪的60年代,法国左派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迦洛蒂曾经详细讨论了毕加索、卡夫卡等人作品中的现实主义精神,迦洛蒂认为他们摆脱了现实世界,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与现实世界不完全相似的特殊世界,因为艺术的根本任务在于表现“人存在于世界”——艺术是人所创造的一种新的现实,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是人在世界上的存在形式的表现。艺术家的任务也不在于复制一种现实或说明一个世界,而是立足于他所生存的现实世界,通过作品表现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按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在吉荣以北京胡同和墙门为对象的一系列作品中,看到的就是他关于曾经历史和现时存在的一种思考。他通过摄影记录生活世界中的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物,这些人和物成为他作品中的基本元素,并最终呈现为一个带有陌生感、距离感,甚至是疏离感的现实世界。有一句关于艺术意义的话语是:“作为个体的艺术家,作为集体无意识的艺术作品”。在吉荣的作品中,包括他通过《景观》系列所呈现的对于“物”的“真实”的追问,以及在相对抽象的《海市蜃楼》系列中所呈现的那种“超真实”的现实,不仅凝聚了他个人对于现实的疑惑、反思以及有关历史的追忆,也呈现了一代人关于北京城市和中国社会时代变迁的集体记忆。
吉荣作品中所散发的这种陌生感和疏离感,同时使我想到了马尔库塞所谓的“单向度的人”。因为在今天,技术的进步和物质的发达已经使我们缺失了反思的力量,技术与消费社会安排了我们的所有生活,传媒和文化产业制造的虚假需求控制了我们的生活,商品正以一种温柔的方式消解着我们的斗志,使我们失去了否定、批判和超越的维度,成为了那种只有认同而没有反思和批判的单向度的人。而对于现实的普遍认同和肯定,以及越来越强烈的对于艺术商品性的追求,也使艺术缺失了否定的态度。但真正的艺术,却必须保持一种否定和反思的力量。曾经的古典艺术,比如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它们以一种对于彼岸或圆满世界的肯定来实现对于现实世界的否定,现代艺术则显现为一种破坏性的否定性。而吉荣以某种“陌生化”的方式所呈现的一个个完全不同于现实社会的超现实的社会,也让我看到了他作品中的反思性力量和否定性力量。
这是我通过周吉荣老师的展览想到的一些东西。再次祝贺吉荣展览取得成功!谢谢大家。
张广慧:感谢主持人,周吉荣老师是我的老朋友,在北京环铁工作室我们作了10年邻居。我对周吉荣老师的作品尽管很熟悉,但在湖北美术馆看他的展场依然是很震撼的。下面谈谈我的感受。
第一,周吉荣老师的作品带有一种荒野的意识。虽然做的是城市题材,但是他产生的感觉是对时间、对人居住的环境的思考,由此产生的视觉距离给人都市的荒野感觉,使我想到了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有关“荒野的哲学”,关于都市人类居住的“荒野”概念植入到人的生活中的反思。我在周吉荣老师的作品里看到了这种倾向,这是他的特点。比如从早期的“胡同”系列过渡到了“海市蜃楼”系列,在这个阶段,突出了荒野意识的概念。
第二,关于媒介的拓展,周吉荣老师是北京最早的一批在外面租借工作室并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艺术家,他的工作室可以看到艺术家背后的故事,与纯粹架上艺术家或者做其他综合材料艺术家的空间不同,更像是作坊或者不同形态的完美集中,包括升降运输材料的电梯、印制大幅丝网版画的轨道都是他自己做的,有点像现代版的达芬奇。制作纸张的巨大的桶,不同的纸源材料的泡制、加工,包括捞纸浆的槽子、机械的传动都是他自己做的。对于材料的拓展,他对每一个环节有如解构的思维,将一个范畴切开若干份,并重构他们之间的联系。将纸张、原土色与荒野意识结合在一起。他做的纸张不是简单的手工纸,倒是像雕塑一样特别厚重,有纹理有记忆感觉的纸,恰恰这个材料是他经过打磨的一种“原”材料,经过他的创作过程,是回头抚摸自己材料的情感呈现。所以他的作品,使我感觉很有特别的温度,这种方法带有对材料的敏感和对材料研究基础上的荒野意识的极佳表现,这是周吉荣老师很有特点的方面。
第三,周吉荣老师是对社会有担当、有责任的艺术家。比如继四方工作室以后,在2004年策划组建了中国版画艺术工作室联盟,60年代生的成员有10人,基于当时版画的大背景之下,自发地组合成有各自艺术选择,并依托各自工作室形成的散漫的团体。目前有3个成员分别在湖北美术馆做过个展,还有一位成员孔国桥担任过湖北美术馆“湖北工业版画三年展”的策展人,还有一个成员苏新平在合美术馆做过个展。这都是联盟成员在湖北的版画活动。2016年受周吉荣老师的委托联系了湖北美术馆做中国版画工作室联盟展,得到了时任馆长的傅中望的支持,“我在——2016中国版画艺术工作室联盟作品展”如期举行。
从这三个方面来说,周吉荣老师既有艺术创作的高度,也有社会的担当,赢得了朋友们的敬佩和好评。最后祝贺展览成功!谢谢!
祝延存:很高兴再次来到湖北美术馆,周老师的展览我很期盼。前几十年看周老师的画,我就很有触动。这些年他在每个题材上的变化、调整我都特别关注,比如说“惊蜇系列”到后来的“海市蜃楼”,再到“中轴线”。周老师这些作品背后所表达的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单从本体语言的层面上进行探讨,可能不是特别适合。本体的背后,艺术家对存在、对生命、对死亡及不确定性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的?每个阶段每个主题的选择,恰恰是无限的思考特别有意义,作品背后有一种诗意的时空沉淀,还有一个隐秘遗迹的人的存在属性,画面上人不在场,恰恰是因为这些遗迹已经消灭掉了或者失去了,我们感受到的那些意象一直在画布的某一个位置上,这个画面能够传递出一些东西,包括时空。他的画面当中有星际、空间,时间性不是随便给你一个主题就可以拿来用,很挑剔,从这里筛选出自己对个人生命能产生内在关联的、有形的、有诗意的属性。周老师是很挑剔的,在语言使用上和甄别上是艺术家非常重要的一个气质,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抛开版画的本体语言,从材料、创意使用上,包括提问的探讨能力结合起来,这个过程很有意思,而作品也呈现了这一重要的思考路径。而以后的退休舞台,恰恰会走到更为自由的表达阶段,找到新的契机,这个特别好。
周老师是我们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第二工作室的老主任,他给与我们这些同仁及晚辈很多帮助,在此表示感谢。周老师有担当、有态度,这一点非常令人尊重。在这个场合之下,表达的是我对周老师画面的解读,他的思考能力,他对画面背后的探究以及提问,他的技术手段在创作过程中产生了什么,他的内在逻辑,他一开始的选择,一直到现在他的内在线索没有偏离,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周老师的后续更值得期待。祝周老师的展览成功!谢谢!
朱橙:谢谢主持人,最近我在写关于周老师作品的文章,所以有些自己的感想。刚刚冀馆长、殷老师、鲁老师以及各位专家几乎都是从材料、媒介、主题、观念这些一直在变化的可见线索出发,但对我而言,吸引我的恰恰是周老师作品所隐含的一些恒量的因素,也就是很少发生变化的框架。这个东西很微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显得神秘,因为属于认知心理学层面,外人难以知晓,甚至艺术家自己也说不清楚。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可能与我接触周老师作品的方式有关。在上个月,为了针对这次展览写点东西,我才第一次见到周老师的作品。不同于那种循序渐进的与艺术家的成长同步的艺术认知模式,我在和周老师完全无交流的情况下第一次就见到了他从80年代创作至今的所有作品,虽然是打包发来的图片。从最开始的《北京胡同》系列,到近年来创作的《景观》系列,在快速翻阅图像的过程中,我所产生的第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北京或者严格意义上是未被现代性侵蚀与割裂的旧时北京会在长达30年那么大的时间跨度中反复出现在不同的系列作品中,虽然形式、形象、材料、媒介乃至观念都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当时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那些有关这座城市的元素和景象,就像记忆的倒带,一直在反复出现,一直在被重新触及。在我看来,记忆就是那个始终萦绕在周老师作品中的东西。所以,记忆是我今天发言的主题和关键词。
首先,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周老师在创作中大量使用了摄影这种媒介,照片的痕迹可以说贯穿了从毕业创作至今的很多系列。虽然照片所呈现出来的客观性和记录性令他着迷,但其实摄影或照片最原初的功能是记忆。当然,这里所说的记忆必须区别于看似是同义词的历史,历史代表着过去,而记忆则“始终是一个当前的现象,一个永远经历在当下的关系”。周老师对自己的创作方法的总体概括是“从现实追忆历史”,这是一种典型的记忆的出场方式。具体来说:
80年代是记忆的生成期。周老师从贵州来到北京求学,经历了七八十年代传统文化的断裂,对于渴望整体传承传统精神的他来说,以自己所生活的胡同及其周围环境为载体的老北京城缓解了他在成长中所经受的这种文化撕裂之痛,并在不知不觉中如印痕般被刻入了他的记忆,让他寻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方位。
为什么这样的记忆来得如此深刻,以至于必须进入艺术的王国?可能原因并不复杂,如周老师所说,只是因为老北京人的生存环境,“犹如一种空寂、孤独甚至神秘未知的梦境意象,在哀挽的情绪中带着一丝淡淡悠远的忧郁意味”,这也是周老师初始建构的记忆,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他的艺术理想。
进入90年代,在这段旧时北京的记忆中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元素,比如跑动的人、新潮的服装、公共电话亭等代表现代的符号。在这个新环境的对比和衬托下,老北京的原有记忆,就像一座孤岛,逐渐走向边缘。对此,周老师采取的应对方法是对之进行记忆的强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惊蛰》到《飘逝的记忆》,从《时空-记忆》到《最后的纪念》,短短数年之间,他对记忆的表现逐渐变得纪念碑化。
可以说,在2002年之前的作品中,周老师不断通过重述来巩固他的理想初始记忆,他几乎是在以档案的形式对记忆进行呈现,他的作品似乎在努力回忆过去,但带给人的感觉却像是,过去并非完全过去,过去似乎再次得到了复活。某种意义上,在周老师的作品中,当前(或现实)本身成了一个被重复、被重现的过去。
对周老师来说,2002年至关重要,在这一年,他开启了具有艺术生涯分水岭意义的《海市蜃楼》系列。这个系列虽然延续了城市的主题,但表现形式及其视觉效果相较前作已大为不同。“新北京”的出场,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现代城市的狂飙突进这个新的现实记忆通过强制性手段对原有城市历史记忆的淡化或消除,这是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的压制性遗忘,借助的不是武力而是所谓现代性的权力框架。
但这种社会性的遗忘并非是如人类进化一般自然而然发生的真正的遗忘,只是暂时性的退场,它的再出场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契机。2011年,北京中轴线申遗文物工程正式启动,正是在这一年,周老师开始了《景观》系列的创作,不清楚他是否受到了申遗事件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有关北京这座历史悠久之城的记忆再度出场了,它以塑造地标性建筑的方式,对《海市蜃楼》中的新北京由于受到现代化侵蚀而缺失地理和文化坐标进行了有力回应。
80年代至今,从记忆的生成到记忆的强化,再到记忆的退场,最后到记忆的再出场,这个过程更像是一种在象征层面产生的、扎根在社会性基因里的“记忆程序”。当然,关于周老师的作品在记忆层面的建构也可放在空间-时间的视角下来审视,比如80、90年代创作的《北京》《时空》等系列,实际上是以空间视角建构记忆,街道、建筑、行人等明显的空间元素,在空间的支配下,记忆的持久性和连续性压倒了一切,而到了《海市蜃楼》《景观》等系列,就变成了以时间视角建构记忆,氤氲、模糊、虚像、不确定的气氛,犹如幻境,指向了绝对的时间,而在时间的支配下,记忆的遗忘、间断性和衰退占据了主导。这个过程实际上经历了以空间为指向的记忆隐喻到以时间为指向的记忆隐喻的转向。
蔡萌:首先非常感谢周老师的邀请,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我上大学时在北京的画廊里看过周老师的作品,当时的印象特别深刻,那个时候我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看周老师的作品。他在版画艺术语言上的探索做到了极致纯度,在这个维度上,我们学版画的人一看这个版画马上会在脑子里产生一串联想,比如它用的什么材料、什么工艺。因为艺术家创作一旦开始会面对一大堆材料问题,就是所谓的物质性、媒介形式,大家谈的内容都跟这个有关。包括做展览也是一样,只要一进展厅,最后面对的就是材料。在做的过程中,考验的全是视觉经验判断和审美创造力。周老师在过去这些年,我也跟他有过沟通。2021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了“重要的不是摄影:中央美术学院摄影纪程”展览,主要想探讨摄影这个媒介在过去100多年,在央美演化发展的过程,央美的这些老师如何借助摄影或者使用摄影这个媒介。其中周老师的创作的“中轴线”系列是最贴切的。最重要的并不是摄影,并不是说摄影不重要,恰恰相反,现在强调摄影之上、之外的那个更广泛、更宏大的主题。在这个意义上周老师的“中轴线”姑且是数码版画,但总是把它当作摄影来看。从物质媒介的角度来讲,版画如果是趋于本体语言,它会跳出版画,周吉荣老师的创作实际上是在努力挣脱本体语言。不是说本体语言不重要,它很重要,是重要的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之后,那就要强调它之上和之外,作为版画的思维、版画的思维方式、版画的复数性、连接性和程序化等等。
最近我也关注到周老师去西北做的创作,这个创作让我突然发觉他开始作为观念创作。关于周老师之前的创作,因为我跟他聊的少,看到的东西有限,我感觉他是用一种天然的材料,因为天然的材料是有灵性的,有的时候是他想成为他自己的样子,或者某种神秘的力量借助了他的手使它成为了应有的样子,他是探讨一种灵性的角度或者带有精神性的或者灵魂性的那个创作,在这个意义上又有一种对观念的创作。我在2021年去周老师的工作室,看到了周老师巨大尺幅的丝网版画,我没见过那么大尺幅的丝网版画,当时非常震撼,包括做的测绘船和天眼。
摄影确实跟版画的关系特别近,今天的数码摄影,我始终觉得那就是数码摄影,包括早期照相制版的铜版画,很有手绘的感觉,很有绘画性的东西,几乎就是一种原作,既是摄影的原作,也可以把它理解成版画,同样是具备版画的思维模式的东西在,比如复数性、连接性、程序化等等都很像。甚至就材料的媒介而言,摄影越来越古典,尤其是传统摄影那一套,应该纳入版画中,去把它放在一起来思考未来的思维转换的影响。昨天周老师说摄影就是版画,因为它有版的概念,底片就是底版,它是有版的。我也是学过版画的人,我觉得学版画的人是天才,因为它的使得我们不被限制在单一的媒介上,这个特别好。在学习过程中,因为每一个版种的差别特别大,学了好多的画种,以前还有插图,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视觉训练。学版画的人真的有一种跟别的专业不一样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几年前我跟徐冰聊过,我说徐老师我看你的创作,背后都能感受版画的思维方式在起作用,我有机会给你策划一个从版画切入的展览,虽然你的作品的表象非常纷纭复杂,比如装置、电影,实际上背后是一个游荡着版画的幽灵。版画在美术学院看似比较边缘,其实是最好的一个专业,对于人的视觉训练、审美训练、艺术训练都特别好。我刚才去楼下看了展览,迅速地在展厅看了一圈,这个展览让我感觉到看到好几个周吉荣。我看到早期做的“胡同系列”,带有一点超现实,但是离现实很近、很写实的。还看到了强调绘画性、抽象,带有点虚无,但是又非常高级感的作品。看到了做得能量特别足的丝网版画的作品,还看到了用纸浆做的综合材料作品,始终体现出他一以贯之的审美品位。虽然变化了很多,但是我也相信此时此刻,包括未来,可能还有几个周吉荣在等着周吉荣老师。谢谢!
周吉荣:非常高兴!感谢专家朋友们的抬爱,把我抬得那么高,各自对我的作品、对我的艺术进行一个全方位解读。实际上你们说到的很多点,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对我今后的创作也是很好的指引,可以吸取里面思想的精华。
这次在湖北美术馆做展览,我很荣幸。展厅很大,让我有点诚惶诚恐,还好我的作品把它撑起来了。此次展览从1987年我的毕业创作到2024年至今,将近40年不同时期的作品比较全面的展示了出来。刚才专家朋友们对我进行了很多解读,实际上我个人来说,我的作品分为几个时期。像我早期的版画纸本时期,持续了有十几年,从安静的北京到已经拆迁的北京,这个历程是我所经历的现实,也是我经历过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那个时期的作品,我尽量想反映我对当时社会的感受、态度,所以我刻意地把带有象征性的,包括“惊蜇”、“最后的纪念”等等这些主题的名称附加在我的作品上,这实际上也是我对当时社会的理解。当然我的方向、我的聚焦点是放在古都北京,它具有典型性,因为它包含了发展的各种因素,早期它那么平静到后来那么躁动,以及新旧交替等等,对我有深刻的影响。
2002年殷双喜老师给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城市的肖像”,从“海市蜃楼”开始,基于这座城市的变化带给我的一种体验的结果,让我对城市的认知有了情感上的转变。很多东西现实发展是一个实体,但是某些方面又存在某种虚幻,这可能在一个新旧交替过程中所带来的困惑。所以我有很长时间在做“海市蜃楼”系列,“海市蜃楼”虽然是一种意象式版画抽象的图式,实际上是表达我所生活的北京的现状,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品。在我作品不断在追求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我是版画出身,可以算是一个根正苗红的版画家。我对技术非常痴迷,对很多版画的技法、技巧了然于心,特别对摄影几个时期的发展跟版画之间的关系,我做了长时间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版画是一个间接性的技术形式,这个门类比较强调技术、强调肌理的美感,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痴迷其中。但是我最后发现它是一种受限的艺术形式,受限于技术,技术的成分那么浓厚,假如说我们陷入其中,就很难以接近艺术的方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想尽量先从材料上进行突破,我从纸上的丝网转变到了布上的丝网,后来又发现没法对版。在这个实践过程中,版画为什么要强调复数,因为版画的复数属性来源于印刷,它是一种传播功能性的技术方式,你成为了艺术,那么这种传播性是否有必要抛开,要立足于技术的话,这个可以放下。我觉得版画的印痕性是一种独特的语言,绘画是达不到的,所以在我的“海市蜃楼”系列实践探索过程中,在布上材料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实际上所有的系列都只有唯一的一个,没有复数性,我也不要复数性。从艺术层面我去让它复制是可以的,但是我挣脱了技术的束缚,我获得了自由,我就不愿意再回到原先的技术层面上去进行艺术追求,这就是我后来逐渐在材料上进行的变化。后来做了纸浆,纸浆艺术不仅是我的个人实践,实际上在我的教学过程中,从2004年就开设了纸艺课。我希望把这种独特的艺术和技术的材料引入到教学里面,它可以形成一种新的门类。这实际上设计了一个问题,版画本来就是一个技术形式,它是印刷转变而来,因为逐渐形成了版画艺术,它就有了各种各样的规矩。就像刚才殷双喜老师说综合材料,综合材料艺委会有规定,要三种技法以上才能成为综合材料。我们要有某些规矩,这种规矩在某些方面可能是有意义的,但是对艺术的终极目标来说它是一种束缚。像杨小彦老师刚才所说艺术的媒介性,这么多年来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发现当我把版画作为我艺术思想的一个表达的媒介的时候,我就自由了,我就不受版种各种技法的限制。所以在后来我做了纸浆的综合材料,利用所在的环境的土壤,比如西北的土壤等等,把它变成了综合体,不完全是某一种门类的艺术形式,我也不希望我的艺术形式归类在一个框架里面。
最后我就想介绍一下,上个月我做了一个项目计划,也是从版画出发,利用孔版的方式沿着丝绸之路,从炳灵寺一直到敦煌莫高窟有五个点,它算是一个观念版画,这中间有我的行为,有我在现场利用现场的材料来制作。当然关于主题,我想丝绸之路跟佛教是不能完全割裂开,因为我的态度不是从佛教徒的角度去做,我是把佛教作为一种文化来进行重新解读,其中剪出了两个小片子,第一个是炳灵寺,第二个是马蹄寺,嘉峪关的长城第一墩,最后是在莫高窟和祁连山之间结束,做了五件作品在那个现场。这对我来说算是一个自我超越。我发现所有的技术不重要,当我面对大自然、面对传承千百年来的佛教石窟,我的观念、我的艺术才最重要的。
谢谢大家!
刘礼斌:晷时印迹—周吉荣艺术展研讨会到此结束,4点半请大家去一楼参加开幕式。
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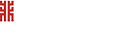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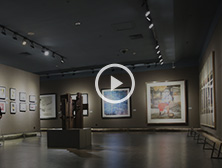
 鄂公网安备42010602000704号
鄂公网安备42010602000704号